戴维•R.马拉斯(David R.Mares),加利福尼亚圣迭戈分校政治学教授,该校伊比利亚和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墨西哥学院教授和研究员。 1982 年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与国防、毒品和违禁药以及南美能源一体化等问题。主要著作有《透视国际市场》《暴力和平:拉美军事化的利益议价》、《拉丁美洲与和平幻象》《从冷战时期来:新世纪的美国-智利关系》(合著)等,同时他还负责了一个有关拉美研究丛书的编纂工作,在拉美研究领域享有盛誉。
哈罗德•A.特林库纳斯(Harold A.Trinkunas),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和拉美项目主任,其研究重点为拉美政治(包括外交政策、治理和安全等领域)。近年来着重研究新兴大国巴西的崛起之路的成败得失,以及拉丁美洲在能源政策、药品改革和互联网治理等问题上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特林库纳斯还撰写过有关恐怖主义的融资、边界和无政府区域等方面的文章。
熊芳华,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葡语系讲师,巴西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2010 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2012 年赴奇切斯特大学进修, 2013 年赴澳门理工学院学习,通过由巴西教育部主办的葡萄牙语水平测试考试,并获 Celpe-Bras 高级证书。 2014 年至 2016 年赴巴西,任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 2016 参与了国内第一本《巴西黄皮书》的撰写。
蔡蕾,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 1997 年 6 月毕业于湖北大学外语系,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2005 年毕业于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2006 年赴荷兰特文特大学进修,获理学硕士学位。 2014 年 6 月毕业于武汉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主持或参与十余部英语教材编写。此外,还于 2004 年参加欧盟组织的亚欧口译项目培训,获得欧盟颁发的口译证书。
张森根,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1961 年和 1964 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史研究生专业。著有《领悟多元视角下的拉丁美洲》,参与出版的译著有《简明拉美史》《现代拉丁美洲》和十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七章 崛起之路:巴西缘何失败又该何去何从(节选)
巴西屡次崛起尝试的启示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巴西一直渴望成为在国际秩序中具有影响力的强国。在 1907 年的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上,巴西是主张主权平等原则的主要发声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试图用最先进的海军军舰装备来支持这一主张。在一战和随后的凡尔赛条约谈判中,巴西试图影响国际秩序的重构,并希望以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方式获取强国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同样,在二战结束之后,巴西一开始并未强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自从这扇希望之门一经罗斯福打开,瓦加斯(以及随后一直至今的巴西领导人)就开始不断争取国际社会对巴西强国地位的制度性认可。
尽管巴西渴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少数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它一直以来都希望创建一个“主权平等”至上的国际制度。这也与巴西一贯提倡的国际秩序一致,即该秩序不需要强迫和收买成员国,而且包括强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自愿遵循同一套规则。从本质上讲,巴西更希望该秩序能够遵循第一章所述的四项基本原则:主权、主权平等、国际和平、以及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但是,它很乐于摒弃美国主张的基本神话及其自说自话的规范,因为这些都是为美国这个领先强国违反规则而逃避惩罚所提供的掩饰。这种做法将会导致产生“薄弱”的国际制度,所能提供的集体利益十分微薄,但这符合巴西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最大限度自主权的愿望,且可以将其参与的成本降至最低。
巴西也从来都不是一股革命力量,它从未像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纳粹德国或是前苏联一样企图推翻现有秩序。但它追求的目标确实不仅限于改革现有的机制,也不仅止步于通过自身参与对现有机制进行微调以反映其上升的力量。它希望将主权平等的规范置于所有其他规范之上,从而对现行秩序基础神话的相对重要性进行修订。然而,由于主权平等的规范已经植于该体系中,所以巴西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修订主义。巴西还试图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其他领域进行温和修订,但同样,这一行为也并不以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一种强调减少贫困、重视社会包容并且为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争取更多利益的社会民主变体。
罗伯特·基欧恩(Robert Keohane)曾经将维护现行国际秩序并提供公共产品的核心国家集团定义为“K集团”。巴西显然希望成为现行“K集团”的一部分,却不愿承担秩序维护的成本,抑或是为此发展所需的各种能力。历史上,现任强国对巴西的这一外交政策都洞若观火,因此几乎不太可能将其列入“K集团”。而且由于其能力的结构缺陷,巴西也无法迫使现任强国接纳它成为集团一员。
此外,巴西的地缘战略重要性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显著下降,这削弱了其对于国际安全领域和现任强国的重要性。在一战和二战期间,当时的海军和航空技术辐射的作战范围有限,故巴西因其疆域延伸至大西洋的地理特点成为盟军的加油基地。当时特定的冲突性全球特征使得巴西对时任强国具备一定的重要意义。因此,同盟国和轴心国都努力争取巴西对战事的支持与贡献(尽管贡献程度极其微弱)。 20 世纪 70 年代,巴西可能获得远程火箭和核武器力量的潜在威胁,以及进而获得的与国际安全息息相关的硬实力引起了美国的关注。但是,在其最近一次的崛起尝试中,巴西的民主领袖已经承诺放弃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或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胁迫手段。由于其所在的地区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因此尽管巴西继续加大其武装力量投入,但它对国际安全的贡献能力相对有限。正如第四章所述,这使得现任强国可以轻易将巴西在安全领域的倾向性政策和贡献一笔勾销。
然而,通过观察该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其他领域——如涉及全球经济和全球公域方面的表现,我们发现,正如第五章和第六章所述,巴西影响国际制度的相对能力与其在每个特定领域日益增长的力量或重要性成正比。如果我们对本书所述的四个历史案例中巴西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加以比较——一战和国际联盟、二战和联合国、七十年代的“巴西奇迹”和追求核电、以及卡多佐、达席尔瓦和罗塞夫的执政期,我们会发现,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巴西本质上还是一个“规则接受者”,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盟国的协同作战还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与 77 国集团以及更广泛的南方世界的合作。正是 21 世纪初的商品经济繁荣使巴西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排名甚至高于英国和俄罗斯,这貌似为巴西在经济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了一个机遇。巴西相对轻松地度过了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提升了其信誉和软实力。现任强国认为应该将巴西纳入新的二十国集团(旨在取代八国集团成为讨论全球经济政策的最重要论坛)。然而,尽管初期大肆宣传,但二十国集团对世界经济复苏政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复苏实际上基本是依靠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二十国集团也没有对欧洲解决欧元区内的危机产生较大影响。
巴西商品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球需求高涨的时期取得成功,这让许多巴西人和一些外国分析家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他们认为巴西经济将持续增长。4商品价格并未立即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即使在危机之后,主要商品生产商似乎也仍拥有大量的剩余资源和国内购买力。本来商品出口商的需求有望帮助七国集团(俄罗斯退出后该集团,改回了原来的名称)更快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迅速恢复,但随着商品价格走低,巴西等商品出口依赖型经济体暴露出其固有的弱点,无法如预期那样扮演七国集团进口消费者的角色。作为一个经济规模虽大却不稳定的国家,巴西政府似乎无力成功掌舵其多样化的经济进程并使其国内经济具备竞争力。巴西无法激发主要经济国家对它的信心,这反过来也阻碍了其经济决策者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影响。
在贸易领域,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于 2013 年当选为世贸组织总干事。在阿泽维多当选之前,世贸组织已达成共识——该职位的继任者应来自发展中国家。阿泽维多熟知内情的优势为他赢得了这一职位,这为巴西作为构架南北沟通桥梁的主张增加了砝码。然而,就其经济规模而言,巴西并非主要的贸易国家,而南北之间关于如何集成彼此贸易和发展议程的分歧使世贸组织陷入瘫痪。另一方面,在全球公域方面,巴西对亚马逊地区的主权使其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息息相关,而它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体现了它在打破美国与俄罗斯及中国的僵局方面的重要性。当巴西具备适当的综合能力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时,随着其能力的发展,它将能够对国际规则、规范和制度产生影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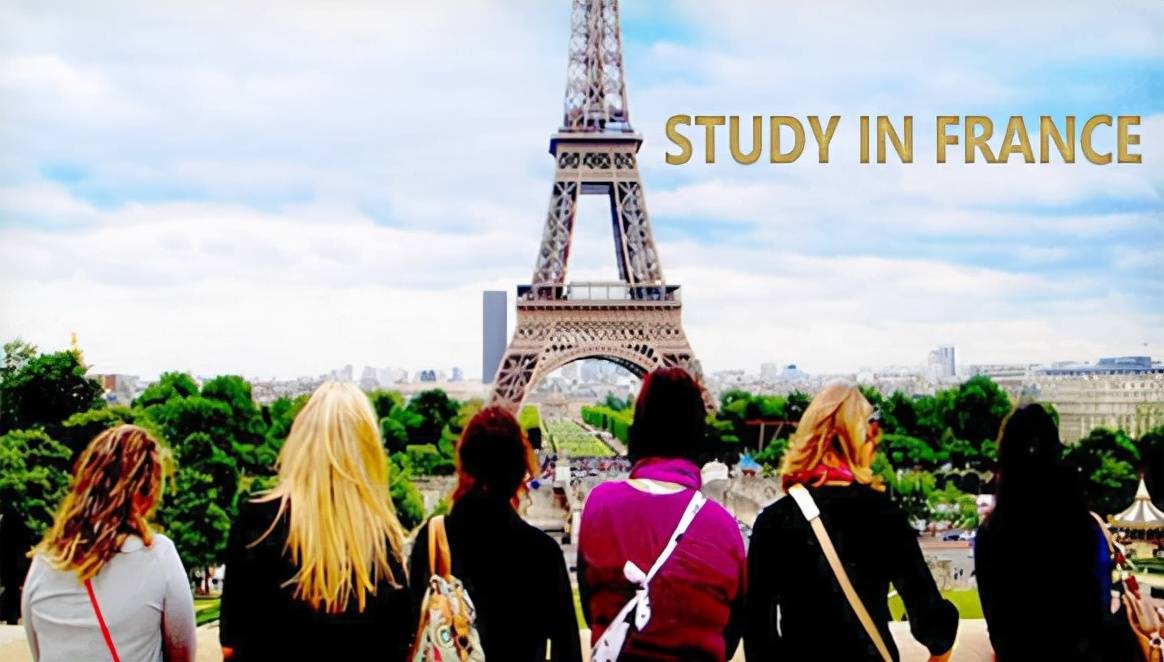
但是,无论是关于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调整的反对(该反对最近才终止),还是国际贸易谈判的主要场所从世贸组织转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巴西在国际秩序上要获取影响力,往往受制于其无法控制的情况。当它好不容易在强国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位时,却常常发现强国们早已转移了阵地,而它也无力阻止现任强国做出这一转变决定。
因此,巴西的国际战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与其在本国所处地区——南美洲所取得的大体成功相比,其全球战略的成果颇为有限。在南美洲地区,巴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精心制定一个反映其愿望的区域制度,各国主权平等,注重地区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旨在促进社会包容、减少贫穷和稳定的文人政府治理。然而即使如此,随着委内瑞拉的内乱及其邻国紧张局势的增加,巴西和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通过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和南美防务委员会等地区性机构,巴西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其唯一的区域竞争对手——美国的影响力。在现行的范式之内,南美诸国正竭力避免那些将引起现任强国注意的违反规范和破坏规则的做法,诸如核扩散、战争或恐怖主义等。因此,巴西可以大胆推行旨在实现崛起的国际战略,而无需担心所在区域内的安全问题。而其他新兴国家,如印度和土耳其,甚至是崛起的中国,都只能对这样的地缘战略地位艳羡不已。
巴西目前的国际战略基础是借助《巴西利亚共识》的吸引力获取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并借此与金砖国家联盟以实现共同努力进入强国议会的目标,但这一战略并没有给巴西带来其渴望的影响力。该战略存在五个本质缺陷,其中四个由巴西本身造成,而另一个则是超出其控制的背景因素。
巴西崛起战略的第一大缺陷是担任发展中国家领导者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但巴西在很大程度上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必要的间接支付来巩固其领导者的地位。由于巴西的经济危机在 2014 年继续深化,且外交部的预算削减过半,因此即使是诸如在加勒比和非洲地区设置使馆,为巴西在多边进程中争取更多合作伙伴的温和做法也被认为成本高昂。就算巴西成功地在强国间谋得一席之位,但由于它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齿数且无法对“搭便车者”实施惩罚,所以其青睐的方案也无法产生成功的政策成果。这是巴西的选择,该选择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各国自愿合作是因为合作适于己身,而不是出于诱惑或被强制参与合作。因此,巴西并未致力于发展和推行“保护中的责任”(RWP)以保持该概念对联合国成员的吸引力。同样,其多边主义的做法也不支持惩罚阻碍解决方案实现的“搭便车者”或国家,例如印度在世贸组织中就农业问题设置的障碍。
第二,正如目前的危机所示,《巴西利亚共识》的吸引力将会快速消失,因为其基础是薄弱的国内体制和仅在高度变化的国际商品市场形势下才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系。巴西的实力曾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因其国内体制遭到破坏(军政府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 2015 年悲剧再次上演(巴西石油公司爆炸式的腐败丑闻和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其国内体制和经济体系的弱点证明,巴西需要一个稳定且合法的政府、多元化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以及为其领导者地位支付短期成本的意愿。
巴西当代战略中的第三大缺陷,或许也是更重要的缺陷,在于它对现任强国,特别是美国的态度。只有当现任强国同意(因为软实力无法强制)将巴西等新兴大国列入贵宾席时,它借助软实力崛起的路径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巴西对主要强国的外交往往掩盖或减轻了其软实力。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西对美国的违规做法持批评态度,或是因为它寻求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修订。有很多美国人对巴西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会报以同情。事实上,在所有新兴大国中,巴西和美国在国内政治和价值观方面最为相似。然而,由于巴西与金砖国家中的威权主义成员国,如中国和俄罗斯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广泛而密切的合作,所以在现任民主强国看来,其软实力因此得以减弱。此外,巴西不愿对其金砖伙伴们的违规行为予以批评,如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或中国在中国南海和东海的行动,这进一步使得巴西创建基于主权平等的全球秩序的主张受到质疑。
第四大缺陷源自于巴西对多边组织机构的偏好。巴西经常是好不容易在某组织机构中赢得一席之位后才发现“游戏”场地已经转移(例如世贸组织和气候变化机构)。这一结果并不仅仅是北方国家转移场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是因为巴西在该领域内没有足够的实力迫使北方国家为此转变付出昂贵代价。例如,巴西在全球服务贸易和制成品贸易中无足轻重,在创新方面也处于边缘地位,因此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能够轻易将最重要的贸易审议转移至 TTP 和 TTIP 谈判(巴西均被排除在外)。尽管巴西一再强调有必要推动WTO谈判,但这些与 WTO 同为多边组织机构的条约涉及范围广泛,与前者相比更能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巴西却始终未能列席其中。
最后,还有一个巴西无力影响的背景因素,当该因素变化时,巴西的崛起前景就随之化为泡影。国际体系中的机遇与威胁千变万化,当巴西因缺乏软硬实力而无法执行其战略时,往往遭遇不利的变化(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后和 2015 年)。然而,即使在这类情况下,巴西也不能逃避所有责任。如果巴西能在国际背景有利的条件下一跃位居高位,那么即使情况有变,现任强国也很难重新设计治理结构将其再排除在外。例如,尽管与首次提议创建联合国和七国集团时的情况相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这三国的相对实力大减,但前两国依然保留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而后者仍然是七国集团的成员国。
由于软实力路径对其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巴西在未来十年能否恢复并再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愿意解决当前模式中的结构性政治和经济短板。这意味着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来重振旗鼓,发展经济。这也意味着要解决政府腐败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以避免不良政策选择和民众不满。
要恢复巴西的增长势头并尝试再次崛起,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在展望未来的同时,显然也需要重新考虑战略问题。巴西在最近一次崛起尝试中所采用的战略并未奏效。
题图来自:flickr
喜欢这篇文章?去 App 商店搜 好奇心日报 ,每天看点不一样的。